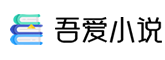连朔猛然转过身的同时,人已经站起来,高大的身躯掀翻了打低的雨伞。
他双目赤红拽住夜歌的手腕,另一手抬起来。
“九爷!”
“连朔!”
秦境泽惊讶地喊了一声,而靳扬一个箭步过去朝着那要落下来的巴掌,迎上去。
然而等了许久,那一耳光并没有落下来。
连朔抬起的脚踹向靳扬胸口。
靳扬身子飞起重重摔在大雨中。
连朔浑身湿透,保持着扬手的动作,攥着夜歌手腕的手背上筋脉环绕,垂着的眼往下滴落雨水,把那张冷硬的俊脸洗刷得苍白没有血色。
他看着夜歌,不知道是不是冷的缘故,他的薄唇僵直,止不住颤抖着,嗓音嘶哑,“闹够了吗?”
“九叔不舍得打我。”夜歌反手用力一拽,人往前的同时致使连朔的胳膊拢住了她的肩膀。
她依偎在男人冰冷坚硬的胸膛里,告状,“我刚刚跳车的时候震到了身子,肚子疼,可能动了胎气。”
“九叔,我的跑车被人动了手脚,是那个万年老二干的,他赢不了我就用这种阴损手段,要不是我反应够快,你真的要替我和肚子里的孩子收尸了。”
“九叔。”夜歌的双臂圈住连朔的腰身,极为害怕寻找依靠般用力收紧,用头顶蹭了蹭男人的下巴,语调娇软又狠厉。
“你要替我报仇。”
连朔闭眼紧抱着夜歌,身体是冰冷僵硬的,心也应该如此,却在这一刻有什么东西在悄然滋长。
这个女孩,从那天在悬崖上到救猫,以及被关地窖和今晚,算计他、引诱他、挑衅他,数次以命相搏,就是想要他的妥协和偏爱。
这一场场博弈,他竟然从一开始输到了现在。
连朔一语不发,弯身打横抱起夜歌。
不同于那次的扛,夜歌的双臂圈着他的脖子,秦境泽自觉地撑了一把大伞在两人头顶。
那个常年位居第二的赛车手,已经被连朔和靳扬的人一起抓过来,按跪在地上。
夜歌的身体是真的有些受不住,脸色苍白,肚子坠疼,闭着眼蜷缩在连朔怀里,快要昏迷过去了。
连朔一步步沉稳落地有声地走向那个赛车手,皮鞋踩在水洼上带起一片白色的水花,溅到正在挣扎喊叫的赛车手脸上。
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在伞面上,连朔在伞下的阴影里,只露出半张脸,抬脚踩住赛车手的手背。
他面上一如往常云淡风轻不带狠戾,却只听见赛车手的手指“咯吱”断裂的声响。
“九爷饶命!放了我吧!我错了……”赛车手嗷叫着,挣脱不了,跪在地上对着夜歌磕头,额头上都是鲜红的血,很快被雨水冲刷干净。
连朔似发了慈悲收脚,居高临下地站着,如能决定凡人生死的神明般尊贵淡漠,唯有一向冷淡的眸里,在此刻摄入一抹悍戾嗜血。
下一秒,整个山谷传来那个赛车手的惨绝人寰的叫声。
几个胆子小的在许久后睁开眼睛,只见地上的鲜血快速被雨水冲走,只剩那僵直苍白的五根手指与主人的手分离,弃于地上。
男人换的那辆车扬起高高如利刃的水花,在夜晚下着大雨的山路上如奔着深渊而去,渐渐驶出众人的视线,一向无法无天的靳扬从怔愣中缓过神,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原来这才是连九爷,上次的挑衅下他还能安然无恙,全靠连九爷懒得搭理他一个晚辈。
在车上秦境泽为连朔处理了伤口,男人皮糙肉厚并不在乎这点擦伤,他一直抱着夜歌。
回老宅后给她冲澡的时候,触摸到她浑身滚烫,吐息灼热,用体温计一量,果不其然烧到了39.3°。
连朔皱着眉给她擦干身子,用浴巾裹着放到床上。
他找了几种平常备的药,手里端着水杯,一条腿放在床上,靠坐着从后面把夜歌搂入怀里,喂她吃药,“张嘴。”
“我不吃药,我怕苦。”夜歌别开头,推走连朔的手,转过身抱住连朔的腰,趴到他怀里闭上眼。
“我的抵抗力很强,你抱着我睡一觉,明天早上我肯定生龙活虎,天灵盖都能给你拧掉。”
连朔一点都不觉得幽默。
他抬手掐开夜歌的嘴,把几粒药片掀进去,灌了温水,再合上夜歌的嘴,紧紧按住。
连朔确定她吞咽下去了,才收手。
但连朔刚放下水杯,夜歌的胃里就一阵翻涌,推开连朔的钳制,身子一歪趴到床畔吐起来。
她吐得掏心掏肺的,没什么食物,都是黄水,刚吃下去的药也完好无损一粒不剩地吐了出来。
连朔面无表情地拍着夜歌的背,来回抚着她的头发,叫佣人进屋打扫。
然后他再拿了同样的药,用刚刚的方法又喂了夜歌一次。
“我看你就是想趁这个机会害死我肚子里的孩子!”夜歌的肠胃排斥得厉害,趴在床畔又吐了。
她浑身都没力气了,脸色苍白,生理性泪水流出来,瞪着连朔控诉,“你给我吃这么多药,就算不会导致胎死腹中,孩子生下来也个傻子。”
连朔平常不跟夜歌在言语上争执,此刻也在竭力克制,目光冷淡中带着嘲讽,“我不想留这个孩子没错,但更想害死孩子的是你自己,你要是真的在乎孩子,就不会一次次去玩命,现在这个结果全是你自己作的。”
“我自己有分寸,是你一直在小题大做,因为讨厌我的所作所为,要我保持人设扮演好褚歌,所以我夜歌做自己的任何事你都要管。”夜歌挣扎着下床,脱了身上的睡衣扔向连朔。
“可我告诉你,我不是褚歌,我是夜歌,我就是我!”夜歌从柜子里找到衣服穿上,头重脚轻整个人很虚浮,强撑着打开门走出去。